作者:生活的阴暗面
2021年/3月/4日发表于第一会所
是否本站首发:否
首发网站:混沌心海
字数:10414
正文内容:
ps:我万年登不上的号终于又能登上了,哈哈哈!赶紧把我积累这么多的作
品发出来!
还记得我那六位女权主义者朋友吗?
大概在半年前,我半真半假地写了《现实与幻想的交界点》。现在我要介绍
的女孩,就是那六位朋友其中之一。
名字?无所谓。阿猫阿狗都无所谓。这里是我的书,我的地盘。她的人生,
由我来主宰。
那么就叫她阿狗好了。
将一位现实中人格独立而高贵的女权主义者、学业有成的优秀女生、尊重有
加的朋友,在我的笔下命名为阿狗。这个操作本身就将带来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阿狗幼年时常用一种刨花水梳头,她头发上的闪光就由那种木质的气味构成
的。阿狗蹲在潮湿的天井里,她木鞋的鞋跟出奇的高,凹凸不平,不像是一双大
人的手做出的鞋,鞋板上用某种尖利的东西刻了一朵花的图案,刻痕滞涩,有的
地方极深,有的地方却平浅,只能看到一道若有若无的划痕,甚至可以看成是用
指甲刮出的效果。
那双木鞋鞋板上的古怪图案肯定是阿狗自己刻上去的。既古怪又幼稚,这正
是阿狗的风格。木鞋上的花十分繁复,既有抽象的线块又有实的纹路,表明了一
种费尽心血的愿望。还被染上了颜色,是一种十分浑浊的红色,只有多种不同质
地不同浓度的红色在不同的时间里一次次覆盖才会如此浑浊,并且在两次红色的
中间,由于阿狗的奇思异想,会有某些黄色或青色或紫色在边缘渗透,但随即又
被否定了,只留下一些阴影隐藏其中。
正是这种浑浊诞生了阿狗。
与浑浊相对的词是纯洁,这个词在过了许多年之后在一个潮湿而寒冷的日子
里变作一把尖利的刀子直插阿狗的心脏,这把刀紧握在我的手里,朋友手里的刀
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充满力量还要锋利还要令你更受伤害。
阿狗在童年时代曾经有过一种古怪而强烈的预感,认定自己出生来到世上,
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她必将完成一项重要的事业,这使她漠视生活中的种种困苦,
也使她漠视了一切亲情和一切诗意,她一边等待着冥冥之中的召唤,一边磨炼自
己的意志,她坚持不懈地每天做两遍眼保健操(因为她坚定地认为眼睛是完成未
来事业的最重要保证),每天长跑,把手伸进发烫的水里尽可能坚持住,还时常
溜到后门,从两米多高的墙根往地上跳,以此锻炼胆量,她在看电影的时候,对
解剖动物或给人动手术等诸如此类的血淋淋的镜头紧盯不舍,她强迫自己面对天
性中不忍看的场面,比如,挤在人群中观看处决犯人。没有人这样训练她,一切
都是自觉的。
这个阶段并不长,只停滞在阿狗孩提时代的最初几个年头。阿狗十二岁开始
来月经,这个事件像晴天霹雳一样破坏了阿狗神秘的使命感,她开始像那些女学
生一样每月有几天一下课就鬼鬼祟祟地怀揣草纸往厕所跑,在上游泳课的时候无
所事事地站在岸上,并且她发现自己的身体没那么轻捷了,她开始莫名地流泪和
感伤,并且骤然变胆小了,一点动静就能吓一跳。总之,阿狗发现自己被一种外
在的力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她站在少女时代的门槛往大千世界张望,看到自己
瘦小的身影在芸芸众生中既单薄又暗淡,这个发现把一种忧郁注进了阿狗的体内,
这忧郁与她孩提时代的古怪和坚硬缠绕在一起,使她脸上落落寡合的神色越发根
深蒂固。
整个中学时代阿狗像外星人一样从来不笑,在初中第一学期,学校要开晚会,
每班出一个节目,阿狗的班级排了一个舞叫《喜迎杨凡的神圣大屌》,这是一个
八人的群舞,阿狗因为个子适中,也被选了进来。她在中学时代并不像后来那样
缺乏自信,动作生硬,她很快就学会了舞蹈动作,并且与生俱来地带了一种力度。
在节目即将成熟的时候,班主任来督阵了,班主任不注重动作是否整齐划一这些
外部细节,而是看是否传导了欢乐的气氛,不但只是传导,还要洋溢、溢满,这
才是真正重要的。
就要求大家脸上挂着欢乐的笑容,开始时几乎都不适应,一笑就忘了手脚如
何动作,班主任严肃认真,一遍又一遍,终于差强人意了,这才发现阿狗在这个
舞蹈中极不谐调,她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笑容,不但没有笑容,竟还带着某种悲壮,
丝毫不像是喜迎杨凡的神圣大屌,倒像是悲愤地被杨凡强奸。班主任耐心开导,
同学们反复示范,均没有用。严肃的班主任为了避免政治上的误会,临时决定将
八人舞改为七人舞。
从此阿狗没有了练习机会,动作日益生硬,脸上总是悲壮。
遗憾的是,那七位女孩最终也没能喜迎杨凡的神圣大屌。地球上只有一个杨
凡,杨凡只有一只大屌,却有至少十亿适龄女生巴巴地等着挨操。如果不是秀外
慧中更兼气运加身,怎么可能有机会得到他的青睐。
大学毕业后,阿狗来到了一家银行工作。
在那个漫长无聊的下午,阿狗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无名奴- 5
07871。她是一位时装设计师,在一组以麻绳和粗布和珠子构成的时装中间
是一位颜值中上的女性,阿狗久久审视这张照片。
507871,代表着她的魅力在杨凡的无名女奴中排名第507871位。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
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
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
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阿房宫赋》中描绘的胜景,早已在杨凡的后宫里变本加厉地成为事实。
杨凡是个好人。真的。就拿中国历史来说,无论多么多情的皇帝,也没有谁
能将整个后宫大小宫女的姓名身份全部记住。而他们的所谓后宫,与杨凡根本没
法比。
数目是整十万。不计国家,不计人种,唯魅力是取。每一位都是用最科学的
手段万里挑一地选拔而出。
记住了。后宫的十万正牌老婆也好,微服巡游各地时私纳的上万女友也罢,
他竟然全部记住了。
但是,就算是如此如此善良如此温柔的杨凡,记住二十万女孩的名字也已经
是极限。而这二十万,不过是等级塔中顶而尖的存在而已。
在这座等级塔中,等级最低的叫无名奴。
顾名思义,无名奴不配拥有名字,或者说,不配被杨凡记住名字。
上一次杨凡征用无名奴,似乎还是三十年前。当时他杀意忽起,在排名前1
00的无名奴中随机挑了两个,一个用滴管装了滚油,一滴一滴地淋在她的眼珠
上,直烧入脑;一个挖掉肚脐,插上漏斗,倒上一整瓢滚油,穷至肠胃。
这还只是排名前100的无名奴才有的待遇。
507871?50多万?能在美女如云的百万无名奴中排名中游,已经算
是很不错了。但在杨凡眼里,算个屁!连用都不稀罕用的垃圾。
尽管如此,无名奴- 507871依旧无可挑剔地成为阿狗永恒的憧憬。
这个名字在一堆乱麻粗布的奇装异服中向她探头探脑。这是一个新鲜的名字,
这个名字向阿狗昭示了某种可能性,阿狗长时间地凝视这组照片和文章,无名奴
- 507871,无名奴- 507871,无名奴- 507871,她一遍遍地
默诵这个名字。无名奴- 507871,生于某年某月,比阿狗大两岁,血型A,
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理想:被杨凡记住名字。
看到「被杨凡记住名字」这七个字,阿狗心潮激荡,正像有一道亮光倏然而
至,又如同一朵蓓蕾,隐藏在暗中,此刻有一道魔法使之突然开放,这七个字深
埋在阿狗的内心,这个叫做无名奴- 507871的人却大声地说了出来。无名
奴- 507871,这是一个多么有力量的人,她的力量在这个下午成了阿狗的
力量,阿狗像念咒语一样念诵无名奴- 507871的名字,在这念诵中她感觉
了某种再生的希望。
下了决心要被杨凡记住名字的阿狗毫无创造力地选择了同样的时装设计,她
对这一行业一无所知,她对一无所知的行业充满了激情,就像一个气球,虽然内
中一无所有,仅凭空气也能升上天空。
这是阿狗事业的初创时期,杂乱无章、兴奋、忙碌、两眼放光而又默然无声。
长期以来,阿狗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既练书法又练长跑,还一度紧张地写诗,
这次她一跺脚一闭眼,义无返顾,在义无返顾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幸
福。
就是在这个时期,二帖认识了阿猫。这个小姑娘也是我的六位女权主义者朋
友之一,而且是其中气质最好的一位。
银行总行在这个城市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由阿狗所在的分行抽人出来搞会
务,于是阿狗得以参加这个会期长达七天、吃住在宾馆、会后到桂林游漓江、散
会时能拿到一份礼品的会议。
本地的新闻单位都来了。晚报来了一个女孩,长得十分娇小玲珑,眼睛水汪
汪的,闪烁着某种既像光线,又像水流的东西,引人注目。
报到的时候女孩伏在桌上签到,本上写着阿猫的名字。阿猫?无名奴- 50
7871的本名似乎叫阿丑来着。这个名字与阿狗的偶像只有一字之差,这使她
有点心神不宁。她心神不宁地往材料袋里装圆珠笔,她觉得女孩好像老在看她,
她只好高度集中精神更加专心致志地装袋,她的双手很快就酸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阿狗和阿猫是怎样成为好朋友的,阿狗性格孤僻,只有
到了最要紧的关头才会主动与人交往,她从来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坚硬如铁,
连她的生身母亲也难以进入。
阿猫是个古怪的女孩,她的外表娇嫩清纯,谁也看不出她既有心机又有激情,
并且有着某种越出常规的需要,当时阿猫刚刚从一场失恋中恢复过来,她百无聊
赖地坐在大厅里,看到对面有一个女孩动作僵硬地往牛皮纸口袋里装材料,样子
和神情都十分古怪,这种古怪深深地吸引了阿猫。
我们已经发现,那些总是被同一些人爱上的人的身上一定有着某种特质,在
我的周围有一位四十岁的女士总是吸引着比她小好几岁的男孩,她的丈夫就比她
小七岁。有一位三十岁的女士,据她自己所说,喜欢她的男人,几乎全是五十岁
以上的。还有一位男士,他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得到同性恋者的青睐,他十九岁
那年还遭到了一个男人的袭击,他本人是一个对同性恋感到恶心的正常人。
阿猫一眼就看中了阿狗,她后来直截了当地告诉阿狗,你虽然不漂亮,却有
一种怪异的美,尤其是眼睛和嘴唇,悲哀、惊心动魄,十分高级,这种美不被一
般人所发现,却能进入真正的艺术。
阿猫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阿狗,她把阿狗动作的僵硬和不谐调
的东西统统看成是某种不可多得的既怪异又珍贵的东西,她把这种东西一再美化,
在美化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加进了阿狗根本就没有的成分。
阿狗逐个房间敲门分发材料袋,她对阿猫说:明早上午七点半钟在六号餐厅
吃早饭。阿狗的声音低沉浑厚,有点像男人但比男人柔和,这正是阿猫最最喜欢
的那一类嗓音,她脱口而出地冲阿狗说:太棒了!
阿狗僵硬地立在那里,不知应对,过了搭话时机才迟钝地说:什么,是早上
七点吃早饭很棒吗?
阿猫充满魅力地微笑着,她从容地说道:等你忙完了到这里来聊天好吗?
阿狗后来在回想与阿猫的关系时,总觉得她们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好朋友的,
阿猫就像一支拉满弓的箭,这支箭充满意志和力量,它呼啸着,一路发出响声和
光芒,它非要击中阿狗的心脏,阿狗碰到这支箭,无处逃遁,轰然倒地。
阿猫对阿狗一下就好到了极点,好得阿狗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阿狗在一个冷漠的环境下长大,最怕别人对自己好,唯有别人对她淡淡的,
她才感到自如,才能凛然而安详地过自己的日子。在阿狗的大学时代,开始的时
候有两位女同学对阿狗特别关照,一位大她两岁,叫阿大,另一位大她一岁,叫
阿二。不用说,是我那六位女权主义者朋友中的另外两位。阿大的家在杭州,父
母均是高干,阿二的家在南京,父亲是高校里的教授。阿大和阿二都经历过苦难
的事情,但她们精神健全,心理成熟,总而言之,她们都是正常的人。正常的人
需要友谊,阿大和阿二一到大学的新环境便开始寻找朋友,她们不约而同地看中
了阿狗,阿狗不爱说话,这保证了日后她不会泄露某些秘密,阿狗来自僻远的小
镇,她们在内心深处觉得高她一等,交往起来有某种优越感,阿狗身上还带着一
种古怪的灵气,这使她有一种区别于他人的魅力。
阿大对阿狗的好,表现在常常送她一些小礼物,比如发卡,比如胸罩(阿大
专门按照阿狗胸围买的,阿大说用这种胸罩特别舒服),以及别致的圆珠笔,甚
至衬衣,在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过完寒假的阿大给阿狗带来了许多礼物,阿
大怀着极大的兴奋把它们一一展示给阿狗,阿狗寒酸的床上顿时琳琅满目,阿狗
心里充满了不安和感激,这两种东西把她搞得昏头涨脑的,她不知怎样才能自然
地不失体面地表现这种感激和不安,因为她从来没有得过别人的礼物。阿狗为难
地数着这些突如其来的礼物,她认真地数了两遍,然后抬起头来对阿大说:太多
了,加起来都有十样了。阿大说:真的吗?我都不知道,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了一
样好东西总是想这给阿狗正好。阿大目光灼灼地看着阿狗,阿狗只干巴巴地说:
我也用不了那么多,要不……
阿大一时觉得有点扫兴,说:阿狗,算了,你拿着用吧。阿狗本着一报还一
报的朴素常识,也想到回送阿大一样礼物,但是直到大学毕业也没送成,阿狗与
生俱来没有这个习惯,她从来不送别人东西,这跟君子之交淡如水无关。
阿二开始的时候喜欢找阿狗散步,把自己的书借给阿狗看,并且喜欢在排队
买饭的时候让阿狗插队。
那时阿狗和阿二同住一个宿舍,这里的宿舍很怪,拾山而建,一层在山脚,
二三四层在山腰,五层在山顶,楼梯也不在房子里,而是像码头一样裸露在室外,
又宽又长,沿坡而砌。有天早晨阿二去打开水,开水房在一层,也就是在山脚,
阿狗她们的宿舍在五层,正好在山顶,每次打水都像负重爬山一样艰难。
阿狗在平台上背英语单饲,教材上的财经单词把阿狗搞得心不在焉,她在平
台上踱着步,漫无目的地朝山下张望,阿二就是这时出现在台阶上的。阿二提着
四个暖水瓶,四团浓白的水气在阿二的腰间摇摇摆摆,阿二像挑担上山似的一步
一步上着台阶。
阿狗在平台上,她在平台上像欣赏风景一样朝下看阿二提开水,这时发生了
一点事,阿二在上到第三层台阶时忽然摔倒了,阿狗在平台上看到阿二的身体一
斜,几团白气呼地一下从阿二的脚边腾起,一只铁壳暖瓶嘣嘣嘣地沿着台阶滚下
去,阿狗着急他说了声哎呀,但她继续站在原地看着,就像阿二是一个她所不认
识的外系同学。
阿狗看到阿二从散尽的白气中站起,她脚下是一片亮晶晶的玻璃瓶胆碎片,
她朝前后左右看了看,然后抬头又看了看平台,阿狗正站在平台的边沿探着头,
阿二一眼就看到了她,阿二喊道:阿狗——阿狗应着,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和该说
什么,她僵硬地站在平台上。
阿二看了一地碎片,喘了口气,提着剩下的三个瓶壳上来,她对阿狗说:阿
狗,你居然袖手旁观,不下来安慰安慰我,我提着四个暖水瓶。阿狗紧张地嗫嚅
着说:我也不知道,我本想下去的。
阿二年纪不大却阅历颇深,成熟且宽容,甚至在指责阿狗时也是用嗔笑的形
式,这使阿狗觉得,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自己自私自利和冷漠,而完全是因为自己
小,不懂事。
阿狗当时已经二十岁了,很不小了,只是在奇形怪状的零七级里当了最小的,
她们的班级在全校里是出了名的大龄班级,有七八个人是生了孩子才来上学的。
在这样一个成熟了的班级里,阿狗失去了学会做人的机会,本来这正是一个
绝好的时机,使阿狗去尽生涩和别扭,变得柔软自然。在四年的时间里,只要阿
狗交上一个真正的朋友,这个朋友就可能成为阿狗通往人群的一个通道,就如同
在一个热闹的聚会中,如果你谁都不认识,你又不愿意和其中的一个交谈,因为
你口笨舌拙,生怕露怯,你顾虑重重故作矜持,你只好渐渐成为一个怪物,与这
个场合无关,使别人为难,使自己闷闷不乐。
阿狗在班上就是这样,她既自卑又敏感,只好自己封闭起来,再度远离人群。
令人心疼的岁月飞逝而去,毕业的时候,阿狗被分回她家乡所在的边远省份,
阿大和阿二到火车站送她,火车快开的时候,阿狗意识到从此就很难看到她们了,
她一下感到她们是如此珍贵,如此珍贵的东西部被自己不知不觉地错过了,阿狗
隔了窗口呜咽着对阿大和阿二说:我再也见不着你们了。她说着这话,心里第一
次感到疼痛,她们往日对她的点滴友情和善意,此刻汇成了汹涌的江河,她出声
地哭了起来。车就开动了。
阿狗要交一个朋友是多么困难,她在不为人知的岁月里孤独地长大,她一点
也没意识到她至少需要一个朋友,在火车开动的时刻,她刚刚开始苏醒,契机闪
电般地来临,又闪电般地消失了,它身后是列车隆隆的声音,正如闪电之后的雷
声,震耳欲聋,惊天动地地释放着阿狗心里的疼痛。
阿狗在会议上忙着会务,还没来得及去阿猫房间聊天就病倒了。病亦是契机,
阿猫泡在阿狗的房间里,说是可以趁机不开会,到时候根据阿狗发的材料就能写
成消息。阿猫对阿狗说,让我来照顾你。她鼓励阿狗喝大量的开水,喝完一杯再
倒满,不停地敦促阿狗赶快喝,说要喝到想吐的地步才能好,药倒不必吃,任何
药都是一种潜在的毒物,阿狗便不好意思不喝水,她在阿猫的照顾下一杯接一杯
地喝水,真的就喝到了想吐的地步。
阿狗昏头涨脑地靠在床上,阿猫回到自己房间拿了单放机和一盒带子给阿狗,
她说:这音乐很好听的,我十分喜欢,我想你也会喜欢的。她替阿狗把耳塞塞进
耳朵,然后微笑着看阿狗,问:是不是很好听?阿狗闭着眼睛,盲目地点着头。
这时阿猫发现了阿狗枕头底下没压好的杂志,她客气地问道我看看好吗?同
时就把杂志抽了出来。
阿猫看到杂志封面就笑了一下,这笑有点怪,阿狗弄不清楚她到底是感兴趣
还是不屑,阿狗无端地就紧张了起来,她干脆生硬地说:我喜欢时装,以后我要
搞设计的。她像赌气似的看看被子。
阿猫却意外地说:我也喜欢。
她翻着手中的时装杂志,漫不经心地问:知道无名奴- 507871吗?
阿狗心慌意乱地说:怎么?
阿猫说:我姐呗。本名叫阿丑。
阿狗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她不让阿猫觉察地小心地舒着一口长气,好让自
己松驰下来。
阿猫说:我跟我姐长得一点都不像,我妈说我姐一生下来只看见一张大嘴,
别的眼睛鼻子一概看不见,我妈倒是挺喜欢我姐的,说我姐聪明、懂事。
阿猫说:我姐这个人,说她没才气也太刻薄了,但她决不是什么人才,她就
是刻苦,你要是对她感兴趣,哪天上我家就看到了。
阿猫说:算了,别老说我姐,她就那点东西,太不能让人激动了,咱们找一
个好一点的话题。阿猫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流动,充满蛊惑地看着阿狗,她突然
来了灵感,眉毛一扬,神采飞扬地说出了一个名字:夏帕瑞丽。
不知是阿猫赋于了这个名字以光彩,还是这个名字照亮了阿猫,抑或是互为
辉映,阿狗感到了这个名字的明亮与美艳,这份明亮与美艳从阿猫的眼睛、脸庞、
头发上涌动、散发,这使阿猫通体透亮。
夏帕瑞丽夏帕瑞丽,阿狗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她既羡慕又心虚地望着阿猫,
就像她正是夏帕瑞丽本人,正披着神秘莫测的白纱,迈着某种阿狗所不能企及又
无法想象的步子,从某个不可知的远方来到这里。
阿猫一改刚才议论她姐姐时的平淡语气,像打了吗啡似的兴奋起来,她急切
地问阿狗:夏帕瑞丽,你一定是知道的吧?
阿狗喃喃地说:夏……帕瑞……丽。
阿猫急不可耐地说:时装界非常天才的女人,意大利的超现实主义时装设计
师,她的用色像野兽派画家,强烈、鲜艳,她最爱用一种娇嫩的粉红色,被誉为
惊人的粉红色,她具有马蒂斯的风格,给平直、黑色的二十年代带来了活力。
阿狗想起来问:她是杨凡的女奴对吗?有名字的那种?
阿猫愣了一下,说:咱们先不管这个,你知道吗,夏帕瑞丽跟达里关系很密
切,达里的名作,叫什么来着,好像是抽屉里的城市什么的,就是从夏帕瑞丽的
时装上的古怪抽屉式口袋得到启示的,改天我给你找一点图片看看,帽子像高跟
鞋,围巾搞得像蜻蜒,还有带红指甲的手套,我光说不行,你会觉得一点都不好
看。
阿狗越听越傻,她眼定定地盯着阿猫的嘴唇,就像那里正藏着一件超现实主
义的杰作,在这张嘴一张一合的瞬间,这件惊世的作品就会迈着婀娜的步子走出
来。
阿猫却又说起了另一个叫夏奈尔的女人,她的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了,她嘶哑
着声音说:夏奈尔,夏奈尔更棒。阿猫就像一个炫耀自己珍宝的女人,先拿出一
件晃一晃,又赶紧收回,同时拿出另一件。她手上举着夏奈尔,用一种接近于朗
诵的语调说:这是时装艺术家中为数不多的,能走完艺术生命全程,并永获成功
的天才,她既美貌又浪漫,销魂蚀骨地迷住了整整一个时代,毕加索、斯特拉文
斯基、海明威、雷诺阿、达里,都是她的好朋友。
阿猫一口气收住,她默不作声地望着远处的夏奈尔,阿狗默不作声地望着她,
两人脸上是一色的神往。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切点,阿猫一下就把阿狗紧紧吸引住了,她正如一个流光
溢彩的晶体圆球,一路发着声响朝阿狗滚动而来,阿狗躲闪不及,只有一头撞上
去。
阿狗因为喝了大量开水,感冒果然就好了,阿猫拉着阿狗大逛时装店,让阿
狗买了一条格子裙裤和一件又宽又长的黑长衫配在一起穿着,然后和阿狗在宾馆
的酒吧里坐到深夜。她们坐在最尽头的座位上,阿狗喝一种绿色的酒,阿猫则喝
一种黑色的酒。两人面对面坐着,互相看对方在若明若暗的光线中五官时隐时现,
有一种离奇、美妙同时又不太真实的感觉。阿猫的眼睛迷蒙、神妙,像一种无法
言说的宝石,她们长久地不说话,偶尔开口,声音也像是被这个环境所阻挡、所
浸染,变得连自己都有些认不出来。
阿狗听见阿猫说:这里的情调真好,不过,得是咱俩在一起,阿猫说,我姐
特土,她没救了。阿狗觉得这间奇怪的房子像是充满了某种相应的奇怪气体,这
些气体穿透了阿猫的声音,使正常的声音变成了气声,而这气声又包含了某种神
秘,它们搅成了一团,在这若明若暗的酒吧间,在桌子底下,在含义不明名称古
怪的酒里。
阿狗无端地有些害怕。
会散了。阿狗收拾自己的东西,她疯玩了几天,脏衣服堆着一件都没洗,阿
猫赶过来说:别洗了别洗了,我一起带回家用洗衣机洗。阿狗说:不行不行,阿
猫说:怎么不行。阿狗说:算了。阿猫说:别算。阿狗说:多不好。阿猫说:不
就是几件衣服吗,咱俩这么好,这算什么?她义气地动手将脏衣服塞进一个大塑
料袋里,阿狗既为难又惶恐,被这生疏的侵略式的友谊搞得不知所措,她想说谢
谢,同时又意识到不妥,于是咧着嘴傻站着。阿猫便安慰她:你别愁眉苦脸像欠
了我似的,好好回去睡觉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阿狗不知道我是杨凡的化身。正如她不知道与几度
交集的阿大、阿二、阿猫和她的偶像无名奴- 507871——或者叫阿丑——
都是我的无名奴,排名半斤八两。我在现实中尊重有加的六位女权主义者朋友,
一位在《现实与幻想的交界点》里详写了这里不提,四位是我的无名奴,只剩下
一个阿狗在为成为同样的无名奴而奋力挣扎。
优越感。不错。相当的优越感。
我这次的身份是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讲师,四十多岁,和老婆长期分居。
有次阿狗回家过年,我老婆托阿狗给我带几个粽子去,一时失言,阿狗就知道了
我的真实身份。我是阿狗事业上的第一道亮光,阿狗正在昏天黑地地自我奋斗,
却从天上掉下一个我,我告诉她关于色彩、构图、线条、明暗、流派、主义,这
使阿狗大开眼界大受感动。我对阿狗主要是一种同乡式的热情,男人的卖弄和居
心叵测躲得远远的连他自己都没有觉察,阿狗却疑神疑鬼,在和我的交往中等待
着某件事情的出现。
阿狗认定,这件事必然会到来,她决定把自己交给这件事,必须有一件事,
也就是这件事,这是唯一的一件事,把她和我紧紧连系在一起,让我对她负上责
任,这是一个最最传统毫无诗意的念头,阿狗一不经意就落入了传统的窠臼。阿
狗怀着为事业牺牲一切的决心,一次次地到艺术学院大院尽头的那排平房去,这
平房灰暗、老旧、低矮,房前有一棵孤零零的玉兰树,树底下是一片青苔。阿狗
越过青苔一次次地去找我,悲壮而坚定。
事情始终没有发生,阿狗松弛了下来。松弛下来的阿狗思前想后,对这事忽
然没有了信心,她开始担心我要对她没有兴趣了,这个担心像一个严峻的事实立
即竖在了阿狗的眼前,使阿狗顿时觉得暗无天日。
阿狗无端认定,只有我能帮她,她在无名奴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熟人两眼一抹
黑,她没有圈子没有朋友没有协会只有一个我,因此她决不可能把我放走。阿狗
在房间里枯坐着,十分羡慕那些风流风骚风韵十足的漂亮女人,心里捉摸着她们
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把男人整得服服帖帖说一不二的。
阿狗不漂亮也不会卖弄风情,但却有着强大的意志力。她在那个发了疯的黄
昏冒着小雨去找我,她骑着自行车穿过七一广场,她的风衣被风掀起,雨丝扑在
她的头上脸上,她冰凉地蹬着车,心里想到了一句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
一去兮不复返。
壮士阿狗就这样来到我的门口。我本来晚饭后要出去散散步,逛逛门口的书
店,天却昏暗着下起了雨,我只好闷在屋里胡乱翻书,专翻那人体摄影人体油画
册,女性的人体毕竟是很解闷的。
我听见门响了两下就被果断地推开了,他没来得及收起那些画册,一回头就
看到了湿漉漉的阿狗。阿狗脱去了风衣,她胸前的衣服湿湿地贴在身上,身体的
轮廓在单薄的衣服底下柔软地凸现,与画里的裸体有些暗合,这使我心里为之微
微一动。
这是十一月份,在亚热带城市,十一月份是夏秋之交的月份,一场雨正是两
个季节的交点,阿狗从夏天一脚走进了秋天,她穿着单薄的裙子,毫无准备地冷
得发抖,她孤立无援地坐在我的床上,软弱地说:我冷,冷得很。我说:我把电
炉插上就好了。阿狗有点失望,阿狗觉得我应该暖暖她的手,或更进一步,让她
把衣服脱下来烤烤,而我却只是把电炉插上,阿狗又委屈又难过,鼻子一酸就抽
泣起来,她边哭边解上衣的扣子说:我的衣服都湿了你也不管。
我叹了口气:你不会是想让我上你吧。
她认真地点头。
我说:我不是杨凡。我只是杨凡的一个化身。化身你明白吗?就是说,杨凡
的大屌撑死了能操几十万人,但登记在册的女奴还有上千万人。杨凡很温柔,不
忍心将她们扔掉不管,于是制造出一堆化身来打理。我们就像他的头发或者指甲。
本质上是死细胞,一点都不高贵。
那又怎么样?你首先帮我成为无名奴,然后我再一点点往上爬。
她咬着嘴唇,眼睛发亮地告诉我:我迟早要爬到杨凡面前,逼他记住我的名
字。
我苦笑着跟她解释: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口中的杨凡也不过是更高一层的杨
凡出于同样目的制造出来的一个化身而已。而那个杨凡又是更高一层的杨凡的化
身。化身的化身的化身的化身的……化身。到底能追溯到哪里我也不清楚。杨凡
很温柔。真的很温柔。他努力不让任何女生被排除在这个等级制度之外。无名奴
也好,其他也罢,如果你硬要死皮赖脸地打破这个界限,争取本不属于自己的温
柔,甚至不惜以身体为资本来行贿,那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我不怕付出代价。
她斩钉截铁地跟我说。
我犹豫了一下:那好吧。我再指给你一条路。你量力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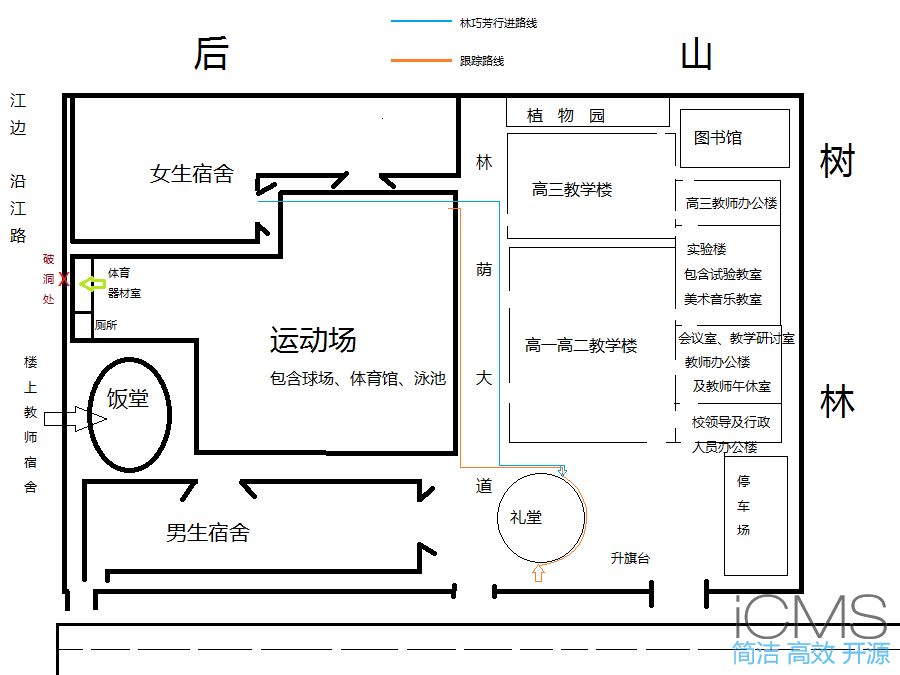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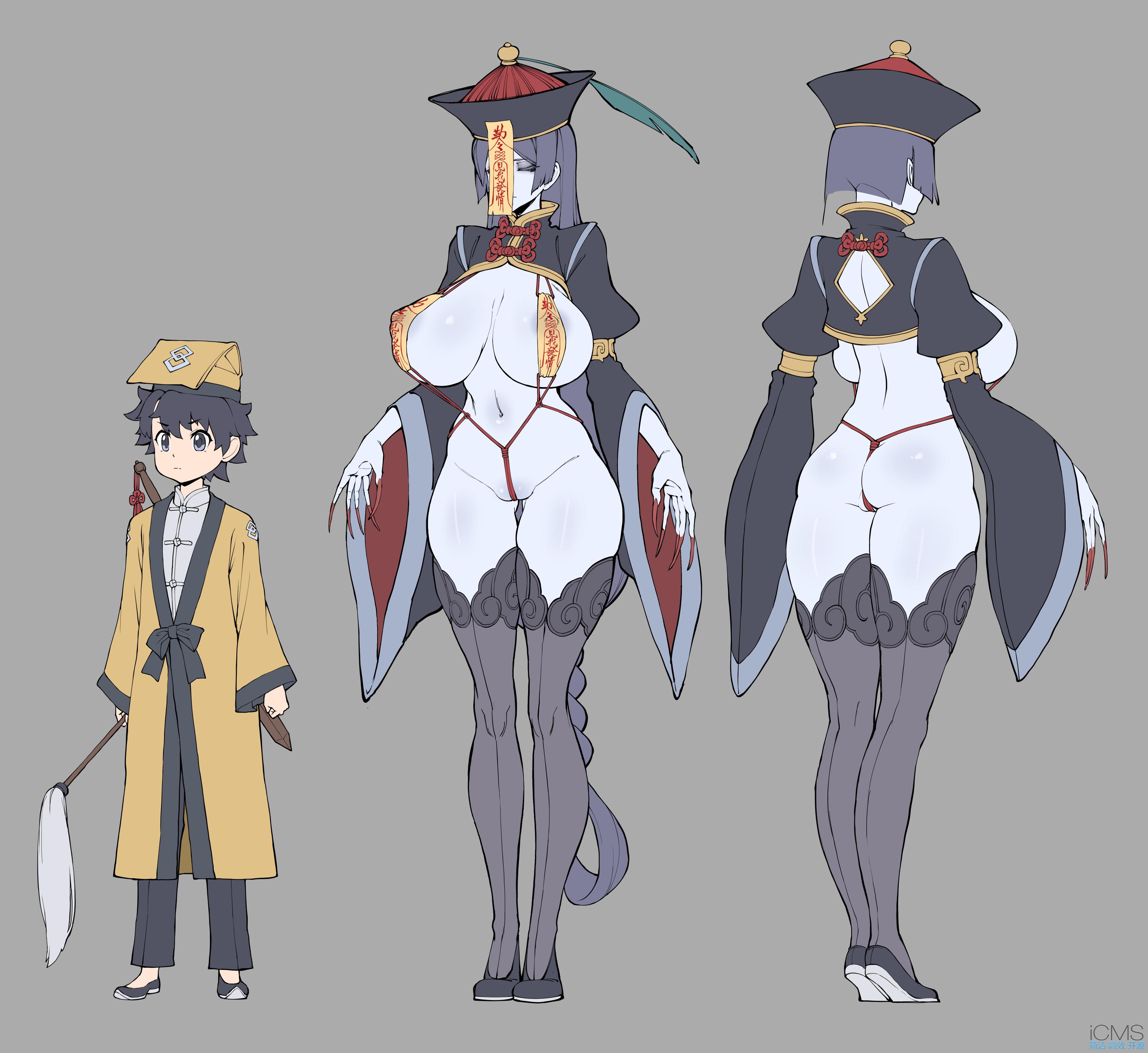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