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朗卿
首发:第一会所
首发时间:2023年4月8日
字数:14,297 字
那梁氏同张洛欢合,不觉已到一更两刻,二丫鬟睡得早,正迷糊着,耳听得
梁氏叫喊,醒了一阵盹儿才睁眼,司玉见司香欲穿衣裳,却把那司香按住到:
「兀自穿甚的衣裳!待会子便又要脱将去了。」
那司香老慢上半拍儿,司玉见司香昏头,便又笑到:「妈妈儿请我俩喝那姑
爷的汤水儿哩……」
那司香耳闻如此,当即喜到:「啊也,造化,造化!既是如此,我等还穿个
甚的衣衫?竟自去罢!」
小淫娃浪性儿起,就连睡衣也剥了个干净,只穿个粉扑扑绣牡丹的肚兜,兀
自盖着俩翘挺的小馒头包儿,司玉见司香色急如此,当下便笑骂到:「你这骚货,
倒不像个没开苞的闺女。」又在司香胯下一揩,确是黏糊糊一片。
「走了,夫人该骂了。」那司玉三两步跨至门前,耳不闻那淫妇叫,只听得
啪啪声响,似扔面团般闷重,那丫鬟一重两轻三声响,便轻轻推开门,见房内昏
暗,便点开屋灯,只见那侄少爷正站在地上,双臂担着那玉山似美妇的双腿,胯
下一根麻赖的大粗棒子,正杵在主母胯下不住进出,那美妇眼里泛白,舌头也吐
了出来,嘴角只剩痴笑,早叫不出来,只听得连哼带喘,好似吃饱喝足的母牛一
般。
那俩丫鬟虽不老实,把那风流快活事也知晓个一二,却连个猪跑都没见过,
更不敢想那风流之事究竟如何,眼见那梁氏神情邪乎,却一发似快乐得紧,便不
管不顾上前,只道那肏屄是一等快活之事哩。
那司玉正待上前,碰见张洛烧着的眼神,不知是怕是爱,一时间竟不敢上前,
只是犹犹豫豫地唤了声「少爷」,那张洛见俩丫鬟到来,心中又是焦急又是紧张,
急是急在射不出精,紧是紧在头一遭当着别人的面儿敦伦,眼见那俩丫鬟含羞带
笑地站在屋厅里,张洛一时间亦羞得进退不得,此时才顾得上去理会那梁氏,见
那骚美人儿双腿乱颤,脚趾都红了,满脸憨痴,好似被抽了魂儿似的,满身美肉
好似云染霞,胯下老蚌好似艳开花,红红肿肿,不住吐着花白的黏涎儿,滴滴答
答垂在地上,胶黏而滑,那张洛心下大惊,怎的肏屄还能把个大活人操死在怀里
吗?连忙把抽屌出洞,把个奄奄一息的梁氏放在破了好几个洞子的软榻上。
「哎哟!你便用这个操我妈妈儿哩!」
那司玉见张洛玉柱暴怒而举,心下甚是惊骇,平素里常听主母聊风谈月,只
说男人的那话儿长也五六寸,短的就如小指头一般,这少年怎得生个这般粗大,
倒与牧场上的牛马相似也?那丫鬟再看梁氏半死不活的样子,心中竟是害怕起来,
司香是雏儿,司玉也未曾通得人道,两下里拽住手,一发踌躇不前起来。
「姨姨,芳姨姨!你怎的了?」那少年见梁氏浑身发软,骨头节儿里发虚,
便连忙上前查验,那梁氏兀自闭了会眼,半晌才倒吸口气,还了阳,却仍是有气
无力,只是躺在那软榻上哎哟哎呦地叫唤。
「我的郎……兀那鸡巴,干奴儿干得甚是不讲情儿里,方才一番,却不是要
把奴家肏死了……方才一试,真真爽得奴家魂儿都要丢了也……」那梁氏说着说
着,眼角竟垂出泪,喜极而泣起来,二丫鬟见梁氏哭出眼泪,还以为主母见欺于
张洛,便不假颜色,面沉似水地盯着张洛瞧。
「哎……哎!好夫人,你莫哭哩……我,我也没做对不住你的事儿呀……」
张洛委屈到。
「兀那肏屄之时,你怎的跟个真驴活马相似也?奴家刚开始还觉着过瘾,到
后来也讨了饶,你却又为何直肏下去?若非收手及时,我目下也已是随我那先夫
去也……」梁氏牝户里余爽未尽,眼上却越哭泪儿越多,那少年心下亦是惊讶,
坏了,想必是肏屄太过生性,把梁氏得罪了,这番却要怎的理会也?
那张洛搂抱住梁氏,把个甜言蜜语哄那妇人,一会儿说那妇人貌美非凡胜似
二八美娇娘,一会儿又夸这梁氏屄里功夫好,一会儿又道那美人儿会爱人,千般
温柔,万种体贴,把俩丫鬟听得直起鸡皮疙瘩,那梁氏虽不见怨怼,耳听少年夸
赞,心下倒颇受用,半晌便破涕为笑到:「你这小子,把哄女人倒有一手,哄得
俺性儿起了,又要找你要,一来二去,我倒要让你的鸡巴吃了,都怪我一发爱你,
你就是把奴儿干垮了,奴儿也甘心……方才行乐,我那先夫一百个,顶不了半个
你,只是你须文雅些,莫要把女人往死里肏便是……」那张洛闻听梁氏说「文雅」
心下不住哂到:「咦!也不知谁方才在那绣榻上叫得村哩,若不是干不过我,又
岂会这般讨饶服软也?想必这淫奴儿也吃了味儿,又恐我不要她,便使话儿把我
哩……」
「知哩,好叫奴奴得知,小子的鸡巴肏干时初还觉爽,干到最后便似麻了般
没感觉,却一发粗胀硬挺,今番还在小子胯下憋得难受哩!」
那少年挺了挺胯,只见那话儿粉柱盘龙,与那结成的青筋,好似作个玉龙绕
柱戏珠的石柱,梆硬里带着半分柔软,昂扬地微微翘着头儿。那梁氏见了又爱又
怕,胯下黄虎穴却已红肿,再堪不得干,便唤两个丫鬟进前到:「你两个平日里
不甚规矩,今日侄少爷在此,你等可近前服侍,休说我没与你等好处,你等得了
侄少爷爱怜,莫要向外传说,倘若泄露了半分,我便要下去,你俩也得走在我的
前头。」
「是哩是哩!妈妈儿,你是大的,我俩都做个小的,一发不敢说与人听哩。」
那司香摆身下跪,又听得那司玉说道:「正是!我俩见妈妈儿垂怜得侍左右,忍
能背主妄语耶?这好郎君端的是个宝贝,我等又怎忍分与她人享用?传说出去,
岂不毁了名声也?」
那梁氏强扶软榻起身,好似能听见屄内呼呼作响,那张洛连忙去扶,却见那
妇人身子一软,玉山般轰然压倒下来,真个是柔若无骨的美熟妇也,那梁氏扶压
住张洛,却只敢把手捺在张洛巨根之上,又呼唤二丫鬟凑至切近与张洛吃屌,二
丫鬟樱桃小口,怎含得住鸡蛋大一个头子?便只能伸舌轻舔,好似吃糖葫芦一般,
那二丫鬟始时皱着眉头,半晌却又对那味儿上瘾,一个舌头好似小蛇一般灵巧,
钻进鸡巴眼儿里,又把个小唇放在缝儿上,紧一口松一口地嘬吸那马眼儿里的汁
水;一个小嘴好似贝肉般轻软,搁在张洛人种袋上,轻一下重一下地啄那杆子下
的肉桃儿。吸马眼儿的风流,发出吸溜吸溜的响儿,亲卵子的柔情,不时还要伸
舌去舔那沟壑,二丫鬟吃得兴起,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地亲吃那鸡巴杆子,大张
开小嘴儿,竟隔着肉棒槌亲起嘴儿来,两下里吮嗦得鸡巴啵啵地响,连个屄疼骨
软的梁氏听了都直觉快活,想来与强男子做事,女子就应越多越好,多出点儿淫
水儿,多弄点骚声儿,看着是一个人爽,其实是四个人快活哩!
「啊哟……啊哟……两位好姐儿……慢些亲我的鸡巴来……」那张洛肏了梁
氏半宿,叫那二丫鬟一挑弄,原本麻了都鸡巴竟又舒爽起来,那俏司玉见张洛告
饶,心下却生出调戏之意来,一边同司香亲玩,一边把个尖葱般的玉指抠向张洛
的马眼儿,细指纤巧,不住擦那马眼儿缝儿,张洛鸡巴外头虽不敏感,却怎经得
这么玩儿的?当下脊柱一阵麻痒,冥冥中只听洒金屑,抛玉尘一般的声响,鸡巴
上又冒出灿灿金光,几乎把半个屋子照得通亮,张洛大惊,一旁的三人却无甚波
澜,好像看不见那异状一般。小天师只觉全身上下遍涌电流,一发过在那鸡巴眼
儿上,那金光亦向头儿上汇聚,只在一点压缩爆发。
「啊!」张洛一声低吼,大片大片泛着金光的精华喷涌而出,喷罩得二丫鬟
身上满是金色,就是驴马射精,亦不似这般量大,可见那张洛绝非凡人,张洛只
觉浑身上下无比通畅,鸡巴上的紧绷感亦随射精渐渐放轻,二丫鬟与那梁氏具是
肉体凡胎,眼中只见张洛大股大股地喷出浓精,那司玉本想惊叫,却吃了一大口
浓精,黏滑地把个小嘴儿都糊上了,精液顺着嗓子下滑,只觉一阵鲜腥之气,和
着浓浓的男子味儿,吃时倒有些上瘾,那梁氏见张洛喷精亦是惊喜,赶忙把那鸡
巴扳到自己脸上一阵乱喷,把个本就百的脸糊得像挂了浆似的,那梁氏尤不满足,
一面裹住龟头吃那精,待到喷精止了,便又把脸上的浓精刮下来吃进嘴里。
「娘也!你怎的吃我的精哩!」张洛见那梁氏一面吃,一面还张嘴给自己看,
虽不甚正经,刺激却是真个刺激,那梁氏吃干了自己身上的精,顿觉倍添精神,
当下又去那丫鬟身上刮了些精敷在自己红肿的屄上,当即便觉得丝丝微凉,不多
时便消了肿,梁氏大喜,便又弄了点精灌进穴内,那阳精涌进阴里,好似琼浆玉
液一般,不止解了方才的疲乏,更觉身心通畅,飘飘欲仙。
那张洛射了精,鸡巴便得了满足,柔柔地躺了下去,二丫鬟被喷了满脸,刚
把眼睛睁开,就见那鸡巴软了下去,不禁亦有些失落。
「郎儿,可能再硬一回,给俺姐妹一遭?」那司玉音带恳求,却遭梁氏斥责
到:「咄!把郎君逗起了性儿,又要折腾我了,侄少爷射了精也累了,你等莫要
纠缠,来日方长,你俩过瘾的日子还在后头,岂在这一时一刻吗?」
「哎……」那司玉垂头丧气,司香也似失了心气儿一般,只得诺诺称是,便
要退下。
「你俩且慢!」梁氏叫住二丫鬟,又自榻边妆奁里取出好似小儿拳头大小的
两锭沉甸甸的银子,一人一个递与司玉司香到:「这两锭银子与你二人,你等可
去打扮得漂亮些,敦伦之事,伤身也补身哩。」
那二丫鬟见了银子,当即雀跃而退,那梁氏回身上榻,却见张洛披着榻上凌
乱的衣裳睡着了。
「臭小子,也不知与情人儿温存,好不知风情。」梁氏幽怨娇嗔,便也上榻
躺下,梁氏喜爱少年体格,更爱男子压在身上,便复搂过张洛,那美妇以情郎为
被,那少年以娇娘为床,两下里依偎,径自睡去不题。
有语则夜短,无语则夜长,情人间两相配合,星转如玉尘飞扬。那妇人领教
了张洛的床上功夫,睡觉也一发甜蜜了,莫说与张洛分别,就是闭上眼睡觉,梦
里不见情郎,那风流妇人亦要害起相思来,及见了张洛,那思春妇倒红脸低头,
一发作个少女般娇俏模样了,只是那梁氏岁数颇长,中年熟妇发起春来,更多了
些拉着丝儿的骚情,莫说入身,就是和那小情郎挨一挨皮肉,碰一碰嘴唇,咂一
咂舌头,她也要泛起春,一发作个床上虎了。
只是那少年实在是龙精虎猛,梁氏经了张洛不知好歹地操干,屄里一发地肿,
连个牝门都作个红糖馒头样红肥,更不敢把那少年的肉棍儿纳一纳,守着心爱的
人儿却欢合不成,那梁氏不禁急得抓额挠腮,愈是着急,那牝户愈不见消肿,身
心煎熬,蚀得那梁氏竟减了斤,先把个壮腰销得紧,又把轮肥臀熬得瘦,眼见着
骚情要把胸前两只玉瓜磨小,那熟妇便害起惧来,那小儿郎最喜咂奶摸乳,这番
要是再瘦了,却不失了其宠幸也?
梁氏见小天师来此不觉已旬日有余,除头天晚挨了他的操,其余几天都只是
同榻而眠,至多不过亲一亲嘴,咂一咂奶,摸一摸鸡巴而已,却把那风流事冷了,
倒叫骚情磨人,那女婿久日不归,恐隔壁的丈母娘见疑,再挨下去亦是讨不得便
宜,那梁氏忍着割肉般相思之苦,嘱那张洛早些归赵家,并把其中原委,一五一
十同那小儿郎讲了,那张洛亦通情达理,见美妇因欲消瘦,又恐赵曹氏见疑,便
点头答允,那梁氏见张洛答应得爽快,以为张洛惦记未婚娇妻,倒闹起脾气,撒
娇撒气起来,那张洛没奈何,便又搂住梁氏一通劝,那梁氏稍舒心些,便也同张
洛搂了,亲嘴咂舌,摸奶撸屌,两下里又腻歪了半日,这才放张洛回府。
「洛郎,奴儿若能风月,便叫司玉司香去你那厢邀你,你可记得情,莫要负
我心意。」那熟妇送张洛出门,又同张洛拉扯一阵,见四下无人,便宽了衣,解
下自己贴身的西罗生洲三角蕾丝亵裤送与张洛,把个小道士臊得面红耳赤,见那
梁氏神情认真,便红着面皮接过那湿漉漉的三角内裤儿,紧紧地贴挨在内衣处藏
好。
「怪哉,西洋娘们儿穿得这么骚吗?」张洛躺在客屋榻上,仔细端详着那刚
能遮住牝阴的三角内裤,那西洲泊来,净是丝袜高跟鞋胸罩小内裤这类女性用品,
不过有一说一,骚还是西洋人骚,想那西洋人多有巧思,倒竟在打扮上下功夫,
张洛不禁一笑,又对着那内裤闻了闻。
「怪香的还,想必我那熟奴奴平日里洗屄洗得勤快哩……哎哟……我的熟奴
奴,你这屁股大的,内裤都比小儿的背心儿大了。」张洛暗喜,暗自对下次幽会
憧憬起来。
正思忖间,耳听得砸门声山响,小道士不禁惊慌,连忙把那三角蕾丝内裤塞
到枕头下,走到房外欲开门。
「相公,相公!」
张洛耳听门外人叫喊,汗毛都立起来,原来那来人是赵小姐,此番若更欲纠
缠,自己怕是逃不脱了,怪哉,一个大姑娘家,怎得如此缠磨俺个破烂道士哩?
那张洛行至门前突然站定,只作屋里没人形状,那赵小姐敲了半晌,竟兀自停下
到:「相公,你莫装假,我眼见你回来,故打扮一番前来就你哩,你兀自不开门,
却不冷了我心?你若不开门,我便不走了!」
「哎,端的是个倔丫头哩……」那小相公叹了口气,径自打开门,见那赵小
姐打扮得尽态极妍,头型服饰一发没有章法,只捡最好看的妆点来,好似那开屏
孔雀,倒如个急乱的锦猫,一行动,便把头上花花丫丫的朱钗摇得如铃铛般响,
张洛见那佳人如此,不禁觉得有趣,便让开身子,迎那倔佳人进屋。
「小姐,那丫鬟姐没同您一块儿吗?」张洛见赵小姐兀自到床上坐好,便坐
到桌旁倒了两杯茶水。
「她有事,不能同我一块儿。」那佳人分明是嫉妒丫鬟抢了风头和情爱,此
番便一人到此,那相公隐隐猜出佳人善妒之意,却也不点破,兀自与赵小姐坐了
个对立。
「小姐此番可有吩咐?」
「多日不见,想你。」赵小姐嫣然一笑,却见眉宇间似有隐隐愁绪,张洛混
迹市井,最是容易察言观色,他虽也爱赵小姐,却不好在成婚前破她身子,便打
定主意,另寻个话儿遮她一遮。
「小姐能惦记在下,便是莫大荣幸,只是我见小姐神情间多有愁思,是否遇
上烦心事儿了?」张洛一席话,说得那佳人眉头一挑,似被张洛说中心事一般,
又仍撑笑颜到:「没……」那佳人轻轻叹了口气,又探身到:「相公,你可凑到
切近与我说吗?」
「可也。」那张洛笑了笑,把个绣墩挪得近了些,那小姐见张洛离得够近,
便不由分说凑上前,电光火石间用手指挑过张洛下巴,「嘤」地吻上张洛嘴唇,
那张洛大惊欲退,却叫那佳人扳住脑袋进退不得,起先还是亲嘴,半晌竟见佳人
伸舌撬开张洛牙关,软舌缠住张洛之舌,啵唧啵唧地深吻起来。
「唔……唔……」那相公起先大惊,半晌竟觉赵小姐舌吻虽生涩,却也青春
大胆,轻柔的鼻息好似春风扑面一般,伴着淡淡胭脂香,透得张洛身子一发地软
了,便更不挣扎,任那佳人品尝佳肴一般咂吸,直到那佳人亲红了脸,轻慢慢松
开小唇,扯出些亮丝,抿了抿嘴,羞答答底下脑袋,更不敢把个眼直视张洛。
那小姐其实是个老实姑娘,只因确实爱那少年,情之所至,才孟浪发情,虽
略略看过春宫,却更不敢破瓜,只是偶尔用指头弄弄豆蔻,青春爱水,一发不可
收拾。那佳人亲了张洛,却不知更待如何行事,便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委在床边,
口中「嗯哼,嗯哼」地轻喘。
「啊也!想来这孟浪的倔佳人,竟是个如此纯情的少女,强亲了我,她倒羞
起来了,哎,好歹是个大姑娘,总是不能白白冷了她面子了。」那张洛被少女强
吻,心下亦是一阵激动,索性坐在赵小姐身边,那赵小姐被个心上人挨得近,不
觉小鹿乱撞,把个九窍玲珑心蹦得都快从嗓子眼儿里出来,那少年虽通风月人情,
却被那少女勾得心肠大乱,更不知如何自处,便轻轻拉住赵小姐冰凉的玉手,兀
自放在口边哈气,那佳人大惊,下意识把手抽了去,又暗骂自己痴愚,不禁后悔
起抽手的孟浪来。
「相……相公……」赵小姐此时此刻一说这话儿,更不似未见之时,只觉一
阵磕巴,小手不禁乱放乱抓,不知怎的就伸到枕头底下,只觉握住个锦布似的东
西,心下不禁好奇,手上一拽,便把张洛藏起来的内裤拽了出来。
「噫!」
张洛倒吸一口冷气,把个乱蹦的心都要停了,那佳人见手上拿了个小背心似
的内裤,先是一懵,进而以为是上次来时自己脱去的内裤,可看那尺寸,直娘贼,
端的长了个好大的屁股,不用想,定是个腚似磨盘的骚娘们,妈了个逼的,正自
风花雪月,没成想竟撞破了苟且,想必那负心汉也早不是个干净的,一发把那童
子之身交去了。
「还没结婚就三妻四妾,端的是个黑心货!」
那佳人本就有些善妒,见张洛花心,气更是不打一处来,那小姐方才还满面
含春,见了裤衩,当即小脸煞白,怒目而视张洛到:「好个风流成性的公子呀……
你这厢乱搞,不怕烂裤裆吗?」
赵小姐一语既出,越想越气,索性腾地起身,抡起玉手「啪」地扇了张洛一
巴掌,把那张洛扇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嗡嗡作响,良久才回过神,便飞速运转
急智,几个刹那间便想好了对辞。
「娘子,你这厢错怪我也!」那张洛登时叫屈,赵小姐耳听张洛叫自己「娘
子」,心下也软了三分,当即叱声高叫到:「如此,却作何解释也?」
那张洛贼起飞智,当即辩白到:「此亵裤之主非是别人,乃是梁氏世姨哩!」
「哦?」那赵小姐耳听是梁氏,心下便又松了两分,兀那干姨年已四九,是
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平素里家风又严,其中确应有缘故。加之赵小姐心思单纯,
下意识觉得张洛只会和与他一边年纪的女子敦伦,那内裤的主人,应是某个青楼
的小婊子,或是随便什么人家的丰腴女儿,她哪里知道世间还有《熟娘少年宝卷》,
更怎想过小马载运大车?当下便复坐下,抱着肩膀,怒目而视张洛。
「此亵裤乃是压胜的衣物哩!」张洛狡辩到:「在下与梁氏世姨夫做了法事,
那梁氏姨姨便病了,便又委我为她作压胜法事挡灾消邪哩。」
「即是法事衣物,一两件外衣便可了,为何要送你内裤哩?」
那小姐耳听张洛以法事相遮,当下便消了气,却又意识到自己方才因误会打
了张洛,心下却又惊慌起来,嘴上倒装模作样地问着,一方面是为了问出点破绽,
自己就坡下驴,另一方面亦是争取时间,好想个能遮掩的借口而已。
「娘子有所不知,压胜之法,愈是贴身衣物,愈是灵验,还有,此法讳莫如
深天知地知,我知她知,此法方才能应验,若不是我也爱重娘子,我本就不应与
你解释,唉,说也说了,若是有什么霉运应验到我头上,我也活该认了……」那
张洛借机倒打一耙,反装起可怜来,赵小姐一听张洛竟会因自己惹上灾祸,心下
便愈加慌乱焦急,当下又羞又疚,两边相激,竟兀自哭了起来。
「我的好相公,妾身错怪了你也……此番千错万错,错在妾身,任那什么祸
害,一发都降在妾身头上罢……我只求相公一生平安,便遂了妾身的心愿了……」
那赵小姐悲声渐大,那相公不禁觉着有趣,却也心疼起来,那小姐虽刁蛮倔强又
带着些善妒,却端的能成个好妻室,当下便主动搂住赵小姐,柔声软语地劝起来:
「哎哟,娘子莫慌……我可是专业的,到时我再作个祈福之法,就把这霉运冲了,
你莫伤悲哩,把个身子哭坏了,我亦心疼不是?」
那张洛劝着,却见赵小姐哭声更大了,张洛心下思忖,此番委屈定不至于嚎
啕,想那佳人来时眉宇间便有些愁思,必是另有隐情,便更不规劝,只是搂住赵
小姐软声问到:「我的个乖乖,眼泪儿哭决堤了是怎的?你便又有甚委屈,今遭
一发同我讲了吧。」
赵小姐听张洛如此问,方才渐息悲声,擦了擦眼泪,无意间又扯过内裤擤了
擤鼻涕,及闻见淡淡女人穴味儿,方才慌忙甩开内裤,掏出手绢狠狠擦了擦鼻子。
「说吧。」张洛放开赵小姐,只是牵住佳人小手,柔声劝到:「我是你未来
相公,不妨同我说说,能办时,我便办去便是。」
「嗯。」那佳人点了点头,却又扯过张洛手臂环于肩头,一面依偎,一面缓
缓道来原委。
原是张洛离家的这几日里出了事,那小相公离家去就梁氏的二日黄昏里,不
知打哪来了个少年书生,自称白山州刘氏子孙,乃赵仓山早年的故人后代,欲进
京城赶科考,行至玄州地界,来此处投奔世伯住宿,那刘姓公子乃是个翩翩少年,
身量亭亭,更兼仪容俊美如少女,那赵曹氏岳母见是故人之子到访,便把那少年
引入内宅,赵小姐听闻有人前来,便躲到门后去看,见那公子确是英俊美貌,可
及至进前时,便能倔出一股妖森森的恶氛,此外虽再查不出个中蹊跷,却仍怪得
紧。
赵小姐觉出蹊跷,便在那刘姓公子走后,私下同赵曹氏说了,可那连未来姑
爷都提防嫌弃的赵曹氏,此番却热情欢喜得紧,把个伶俐佳人的警言充耳不闻,
倒把张洛之事来搪塞,还说什么破道士都容得,故人公子岂容不得?两下里言语
相冲,一向和睦的母女竟吵了起来,那刁妇人话说得急,更有悔婚将赵小姐许给
刘姓公子的意,听得那佳人登时咬得银牙咯吱吱山响,气冲冲地出了屋门。
不过那刘姓公子只在赵府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辞别出府,那赵曹氏千万般相
留,终是未将其留住,可三日之后赵小姐出门去会女伴儿买胭脂,归来时却远远
望见刘姓公子出赵府门,及至回家问母时,那主母却支支吾吾地遮掩,反倒成了
欲盖弥彰的拙戏。眼下赵仓山外出未归,家中只有孤女寡母留守,那玲珑人儿不
由得担心起来,生怕家业让外人谋夺了去,眼下能依靠的男子只有张洛,赵小姐
好不容易盼张洛归来,又于大喜大悲时慌了心神,焦急间联想起数日前的委屈惊
惧,那佳人才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想来我那娘亲受奸人蛊惑,要伙外人给家里来个卷包儿会哩……」赵小姐
说罢,不由得呜咽起来。
「嗯……」张洛思忖再三,谨慎道:「我虽与我那岳母有些成见,可要说一
个忠贞了二十多年的妇人有了家室而不保晚节,我是万不信的,顶多如别的阔太
般使俩钱儿,包了那小白脸儿在外头风流便是,偌大个家业还有个有能耐的夫家,
于情于理我是不信卷包会的。」张洛沉吟片刻,又到:「就是我那岳母再上头,
也不至于为了个小白脸把个身家扔出去……诶……」
张洛猛地想到近日来闹得凶的艳香鱼水派邪教,头前据那女店家所说,那
「黑里欢」拐男拐女,成员里定是男女都有,保不齐另有妖人,见图谋梁氏家产
不成,又来蛊惑赵家主母,那主母虽上了年纪,论姿色也能压过七成少女,保不
齐图财图色的情也有。如此说来,便要提防了,妖法邪祟,自不能以常理忖度,
那妇人保不齐真中了摄法或迷魂法,那时节真就要卷包会了。
张洛念及此,便也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忙扳过赵小姐肩头,郑重其事地叮嘱
到:「姐姐,此番事或许真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委,你在家里更需提防,那小
白脸来得蹊跷,或真是个妖人也说不定,那时节卷了财物,连你们娘俩也要被拐
了去受苦哩……」
那小姐闻言亦大惊,不由得小鹿般扎进张洛怀里,一拱一拱的求抱:「若是
如此,相公,我便再不与你分开了,今后你走到哪儿妾身就跟到哪儿,郎君,万
望你护持奴家也!」
张洛眼珠儿略略一轱辘,便安排赵小姐到:「姐姐,此番你可带几个贴身的
人儿去梁氏姨姨家住下,一来能抱个团儿,二来他家人多有个照应,等你过去后,
我便贴符做个结界,定保你无事。」
那赵小姐微微点头道:「如此便好,相公,你虽与我那娘亲过不去,关键时
节,还望你护持一二。」
张洛诺诺应允,那赵小姐自去同丫鬟打点什物,预备搬家不题,张洛怔愣半
晌,便赶忙翻开行囊,无论甚什物,一股脑翻将出来,又趁黄昏未尽,店家还未
闭门之时,兀自到街上购置了朱砂墨斗线,并包里原就有的黄纸黑狗血,就着昏
登做起挡煞驱魔的结界,那天师借着黑狗血混了朱砂,铜砚台里碾作黑红黑红的
浓墨,朱砂防恶鬼,狗血挡邪神,是个神鬼都挡的结界基质。又借着狼毫枯笔浸
润了墨,一面掐决念咒,一面在一张张黄纸上写满挡煞的符箓,张洛奋笔疾书,
不到半个时辰便写好了符咒,又把符咒借热鱼鳔粘在墨斗线上,和着朱砂在梁氏
府宅边团团围住,又在府门口贴了两张门神画,一切事毕,张洛一摸脑门,竟细
密密的全是汗珠儿。
张洛不迷信法术,却倒是个道学渊博的天师,若论起道法,可比翰林的学究,
端的是个精通儒释道的才子,那天师虽不迷信,却在真真见过妖鬼邪教以后,不
由得把鬼神仙道也信了三分,那道士凭依经典,自觉已做到最好,若非泼天本事
的大妖魔,据书上说,挡几个千把年修行的精灵还是绰绰有余的。
那张洛收拾停当,次日里安排了未婚妻与那熟情人儿同住,那梁氏虽暗以赵
小姐为争宠之敌,却也更疼爱这从小看着长大的世侄女,梁氏无儿无女,便把个
赵小姐当做自己亲女儿一般,故梁氏与赵小姐见面时虽略有摩擦,相处多时,便
两下里都觉亲切和谐了。小相公见二妻相处融洽,亦觉自己有齐人之福,便买了
两朵花儿,一人一个分戴在两佳人的鬓角边,二娇娘两下里欢喜,把个老的喜得
如二八少女,让那小的甜得似食了蜜糖,欢喜毕,却又真如花般争奇斗艳起来,
一熟一少一左一右地攀扯住张洛,都起哄地问谁好看。
「我的天,都好看,都好看行吧,姐姐俏,姨姨柔,小子都喜欢哩。」那张
洛如是答,二佳人却仍是不依,一发叽喳,莺莺燕燕地闹了起来,那张洛更不多
嘴,明着挑住赵小姐的下颌,啵地亲了一口,趁那小娇娘分神,手又在美熟妇的
屁股上掐了一下,既合了佳人的情,又勾了美人的意,真个两下里都欢喜,一发
脸红起来。
「姐姐,姨姨,你俩好生安顿,小子这就要回府照应了。」那少年想着再待
下去说不准又要闹出什么修罗场,心下亦是发虚,便找了个借口溜了,那梁氏把
小情郎目送出府门,余欢未尽,拧腰摆臀往屋里走,那小姐见世姨浪得紧,也不
禁盯住那美妇的屁股看,联想起那条小孩背心儿大的蕾丝内裤,心下不禁旋着升
起一股复杂的嫉妒之心,可望着那又圆又翘的两瓣美肉,连自己都不禁想扑上去,
尝一尝个中滋味。
「好生养的腚,却不见个孩子……」那俏小姐心里一阵慌乱,只好说些话儿
来搪自己。
那张洛自出梁府门回赵府,却见赵府门前的石狮子的脸叫两张白布蒙住了,
张洛大惊,忙问门房何故,那门房只道是主母吩咐,张洛略一思量,便更觉蹊跷,
石狮子守门镇宅,如今却被两张白布蒙了眼,见不得凶神恶妖,自无法守宅护院。
张洛不去揭那白布,却掏出毛笔,回屋取出牛眼泪,并滤过的柳叶汁,另加秘方,
做成两种无色的墨,那牛眼泪可使人见鬼神,亦能觉察蹊跷,而柳树汁则可驱鬼
驱邪,张洛蘸了牛眼泪,给那两张遮盖石狮子的白布上一边画了双眼睛,又用柳
树汁画了两副尖牙利齿,牛眼泪能见,柳树汁可驱,却都是无色之墨,不知秘辛
者自然看不见。那张洛准备停当,便又去向赵曹氏央告,只说自己要回山上看望
师父,却见那赵曹氏并不似往常那样严厉,竟欣然应允,又拿出十两银子,嘱张
洛买些师父喜爱的东西送去,就算是家里心意。
「好家伙,吝啬如此之刁美人如今恁地反常,果真有蹊跷也!」张洛心下一
惊,却是喜怒不形于色,兀自诺诺退去,那少年装模作样地出了府门,绕出胡同,
便悄悄潜到宅门后的小巷,兀自寻赵府翻墙而入,脱去锦衣,换上自己那套不起
眼的道士打扮,虽不知有没有用,却依然照道书上的秘法隐了三魂中的两魂。
据道法所载,人之六感,盖因可觉察三魂七魄,若可隐去三魂中的两魂,便
是径直从人身边走过,那人也不会注意,所谓「灵感」,大抵如此。那张洛射精
之际喷出的金光,只有张洛一人能够觉察,而梁氏与司玉司香更不能查看,也是
因灵感差距。
张洛打点完毕,复揣了点柳树汁和混了朱砂的黑狗血,当即便翻身上墙,凭
依墙头屋檐轻身游走。那少年不仅通经学,更会些脚上轻功,一丈高的围墙,一
窜,一扒,腰一拧,便可轻飘飘地上去,至于踩瓦无声,踏沙无痕,随差了些,
却更不在话下。那张洛踞在屋顶,三两下便到了赵曹氏之屋,居高临下,本欲作
长久打算,却见那赵曹氏封了一袖信,交于贴身丫鬟,复叮嘱几句,那丫鬟方才
出门。张洛见状忙振奋精神,伏在屋后顶压低身形。
那张洛等了半晌,见天色已至黄昏,便不由自主紧张起来,逢魔之时正在黄
昏,那小白脸儿要在黄昏前来,必是同赵曹氏约定好的了,可见那姓黄的非魔即
妖,若是如此,柳树汁,黑狗血,便够他喝一壶的了。
又等了半晌,只听见院门外「啊」地传来一声惨叫,想是那妖人来了,张洛
当即抖擞精神,伏在屋顶听查动静。
张洛又等了一阵,方才见那贴身丫鬟打着灯笼,引着身后一书生打扮的白衣
少年进门,那少年头冠略歪,头发略凌乱,想来方才被吓得不轻,神色里仍留着
慌张,张洛见那小白脸儿东倒西歪的模样,不觉十分有趣,捂着嘴低声偷笑起来。
正自笑时,又见那赵曹氏喜滋滋出屋相迎,及见那少年时,便拉住少年之手笑盈
盈地不放,只是嘘寒问暖,说长道短,把那小白脸儿都说得烦了,那妇人方才屏
退丫鬟,兀自引那少年进屋。
那天师敛声屏气,揭开几张屋顶瓦,顺着瓦缝儿探查屋内情况,只见那刁美
人引少年相对坐在桌前,又是寒暄一阵,便在两个茶杯里倒上茶,柔柔地说起话
儿来:「方才见小郎君惊慌无措,想必是受了些儿惊吓?我院里没有狗,石狮子
也遂了你的意蒙上了,你却又因何怖惧也?」
那少年开口回话儿,音儿里真有蛊惑人心的魔力一般:「正是惧那石狮子也……
方才我进门时,好像被什么东西啃了口一般,还是得缩在丫鬟姐儿的影里,我方
才敢入门哩……」
那赵曹氏闻言笑到:「恁个胆小的男子,见个石狮子也要畏怖也?」
那小白脸儿闻言笑到:「非也,好叫伯母得知,石狮子惧得,女人却不惧也。」
那小白脸儿答到。
「如此,你也是个勇的了?」那妇人见那白衣书生青春年少而又俊美异常,
也不禁心猿意马,一发不想说什么来。
张洛耳听得那刁美人对自己不假辞色,却跟个小白脸儿谈笑风生,两句话就
聊到裤裆里,当下便大为恼怒。
「哦?这么说,世伯母喜欢勇的了?」那小白脸儿笑到。
「略见过一两个罢了,只是见你这般皮肉年纪,倒不像个勇的。」那妇人见
小白脸儿略显孟浪,便矜持到。
「就是我这般皮肉年纪,论风月,也是个勇的,伯母不妨与我试试,定让伯
母欢喜哩」小白脸此言一出,连张洛都觉得那人不要脸了。
「哦?你要怎么试?」那妇人心里明镜一般,却仍强打精神矜持到。
「世伯母有个『花儿』我也有个『话儿』就让我的通通您的,便知道勇不勇
了。」那小白脸儿表情甚淫贱,张洛便打定主意,说甚么也要给那姓刘的来一下。
那淫贼见了赵曹氏胸前隆得高绷得紧,便伸手要去揭那梁氏的胸衣,及到半
路,却叫赵曹氏笑着止住了。
「你这小郎,此厢便如此孟浪,好失礼数。」
「婶子的身子实在美丽,光是见见都觉馋,前几日融洽得甚了,今遭接了您
的信,小侄便来赴您,您却又不让小侄就,却不是折磨小侄也?」那小白脸儿央
求甚哀,赵曹氏便也心软,口里却使话儿到:「我本就喜欢你这读书人,可你也
太急了点儿,约定的,我一定给你,只是莫要孟浪,先风花雪月一番,待到情爱
甚浓之时,两下里欢欣,这才把那事做了,于你于我都舒心哩。」
张洛在屋顶,一字一句听得真,心下不禁暗笑到:「这妇人果然同我那媳妇
儿是亲生母女,做事之时,一发都要先风月,再风流哩。只是我这岳母更矜持,
却不知那王八操的小白脸子抗不抗得住,若真是个孟浪之徒,烦也叫烦死了。」
及再看时,便见那小白脸儿耷拉着眉眼,一脸败相地坐在赵曹氏对面,那赵曹氏
举起半冷的茶,要与那淫贼喝个交杯,那淫贼叹了口气,强颜欢笑地拿起茶杯。
张洛见状便打开装柳叶汁的小瓶,为保险,便对着那两杯茶里一边滴了一杯,
那柳树汁常人喝了无妨,妖人喝了却会破功,淫贼与赵曹氏喝了个交杯,半晌便
觉肚子里炸炮儿般又响又疼,那妖人顿觉不妙,却见那妇人兀自含情脉脉地说个
不停,小白脸儿只顾着肚子里刀剜般疼痛,哪里还听得进半个字儿?只是捂住肚
子,忙求去趟茅房而已。
「哎哟~郎君,情爱欢时,还怼尿得要尿是怎的?」
那妇人只道淫贼憋了尿,便也未甚挂怀,便又牵住淫贼的手,任那妖人的脸
拧得跟疙瘩似的,却更不撒手,只道那小少年扮鬼脸儿逗自己开心哩。
「噫!我那丈母娘忒没眼力见儿了点!把那直娘贼憋得和孙子似的,她倒更
不察觉哩!」张洛强压笑意,更不敢高声,生怕错过好戏,便憋着笑看那淫贼窘
迫。
只几个须臾间,那淫贼已是弯腰捂肚满地打滚。那道士犹觉不尽兴,便捡了
块碎瓦朝那淫贼扔去,小小的石块一打那贼人头,那贼人便似戳破了的猪尿泡,
噗地一声喷将出来,把个白衣霎时染成黄衣,恶臭的味儿熏得张洛都不禁捂住鼻
子,遑论那赵曹氏就在贼人切近,那恶臭熏得干净温香的美人儿脸都绿了,见个
原本还风度翩翩的少年喝了口茶后便倒在地上,前尿后拉地一阵放炮,一股股稀
黄的水儿憋不住,便从裤腿处决堤似的往外喷,咕嘟嘟冒着热气儿地染了一地。
那少年郎倒在地上喷屎,那美人儿赶也不是不赶也不是,便忙扯袖掩面遁走,任
那贼人喷得满地都是屎尿。
「我操!这逼人儿是屎人托生的吗?恁的不住地满地拉稀?」
赵曹氏出了屋犹闻见一股恶臭,便口无遮拦地一边村口泼骂,一边逃出院子,
张洛在屋顶憋得比底下那位还难受,却仍要找些乐儿耍那妖人一耍,便扯开黑狗
血瓶的塞子,顺着瓦缝儿滴下去,那混了朱砂的黑狗血浇在妖人身上便丝丝冒气,
把那妖人激得嗷一声屎里打挺儿,平地里窜起老高,屎尿却仍是不停,噗嗤噗嗤
地把个干净的闺房喷得茅坑相似,就是扫饬起来,没个三五天也难恢复原样,张
洛见那妖人窜儿了稀还能蹦得如此生猛,不禁也是一阵佩服,但见那妖人被黑狗
血烫得皮开,漏处却龇出黄毛来。张洛大惊,原来这小白脸儿是个套着皮的画皮
妖,内里似乎是个带毛儿的动物,套了张画皮,便出来兴妖作怪了。
张洛见那妖人叫沾地后便踩着一地黄屎跑出屋,便忙追那逃窜的妖精出门,
那妖精出了府门,到了没人之处便撕开画皮,里面却是个半人半兽的丑陋模样,
更看不出是什么妖精,想来是个修炼有一定年头,能化半个人形的,否则怎得撑
住那副人皮也?
那妖怪拉了稀,跑了半里便没了劲儿,瘫趴在地上,肛里不住地喷黄水儿,
兀自喘了半晌,才挣扎起身,隐在夜影里,三拐两转地进了个颇雅致干净的胡同。
张洛料想那胡同里便是其藏身所在,便跟在后头,只见那妖精打开一处院门便走
进去,张洛站在屋脊上,见那小院儿倒颇精致,想必大户人家养个外室妻妾,富
太太包个小白脸儿,大抵也都安顿人儿在此处。
那天师恐妖魔进屋找了个什么法宝恢复元神,便趁那妖精刚进屋门的片刻后,
捡起屋上瓦片啪嚓嚓一股脑摔进院子,一面高声大喊「抓妖怪」,又取出火折子
燃了符纸扔到院子里,那妖精耳听得院内啪嚓啪嚓的响,又闻人喊抓妖怪,见那
燃着的符纸照得院子里灯火通明,便真个以为是来人捉妖,便如惊弓之鸟,漏网
之鱼一般「嗷」地怪叫一声闯出屋去,正欲窜攀上屋顶,却到底因为拉稀没了力
气,便只能作困兽斗,回光返照般窜出院子,钻进夜色里飞腿狂奔。
张洛见那妖怪接着夜色窜逃得快,自己眼看要追不上,索性抡圆了膀子,把
个黑狗血瓶整个砸到妖精头上,耳听得啪嚓一声,那瓶正中妖精脑袋,把个妖精
砸得闷哼一声倒地,却在一滩黑狗血中挣扎着化成兽形,张洛借着月光观瞧,原
是只似獾类猹,叫不上来名字的野兽,打去了道行,奄奄一息地躺在一片颜色复
杂的液体中。
那张洛见那妖精如此模样,心中顿生怜悯,又恐那兽物再作乱,便捏着鼻子
赶至进前,掏出小刀挑断兽物脑后妖筋,便放那兽物一瘸一拐地逃了,那兽物没
了妖筋,再怎么兴风作浪,也不过偷鸡摸狗而已,张洛头回出山便降服妖孽,当
即满意地拍了拍手,遂返到哪妖精住的小院里侦查,一进屋门,迎面来便是一股
恶臭,张洛捂着鼻子,点燃屋内蜡烛,那屋里妖气森森的,连蜡烛的火光都叫妖
气染成绿色,冷冷地燃着,没温度般噗啦啦吞吐着火苗,张洛让火光照得心里发
冷,便显了三魂,待到屋里妖气散尽,烛火由绿转黄之时,方才进屋查看。
那屋中装潢颇雅致,梁上吊着灯笼,漆柱妆壁,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
把椅子,那床上除被褥枕头外,还堆着一摞画皮,张洛捡着看时,方见那画皮乃
豆腐皮糊纸浆,另用湿法浸得韧滑所制,乍一看,确像人皮。那画皮有佳人,有
公子,精致浮凸,连性器处都做得逼真。
「噫!这妖精手倒巧,只是做了个女人画皮,通人道时节儿,想必假走的肛
门,怪不得屁眼子收不紧,恁的窜稀哩。」
张洛暗自笑着,又不禁赞这妖精手艺倒好,兀那画皮竟如此逼真,做得真像
从活人身上剥下来的相似,又借着烛火映影儿,见那皮影映在白墙上,两只眼倒
空空洞洞,愈瞅愈觉诡异,便赶忙放下画皮,复又去查它物去了。
张洛走到书桌旁,便见那桌上兀自摆着封粉扑扑的信,纸滑墨香,颇为讲究,
张洛拾起信,便见那纸上之行楷极工整柔美,笔法里又透着老练纯熟,非是从前
常练字的大家,又经累年的习作,断不能有此雅墨,定眼细观之时,便见那信上
写到:妾曹氏言:自上次别,便思郎君。通家之亲,更兼情爱。忘年之宜,亦蕴
款款。今宵佳期正好,吾等便可相会,但见月圆,莫负花好,静待来时,望君采
撷。
另附诗云:绛灌更恋青春好,桃李最是熟香甜。
但求秋蕊承新露,始是熟少欢恋时。
「啊也!这是我那岳母通奸外人的证据!若是除了妖怪再对峙,捉奸无双,
尚嫌捕风捉影儿,今番连实都落在我处,却不是攥把住了?」
小女婿大惊大喜,忙把那信依故痕折了,又寻着那信纸装好,慎之又慎地装
于怀中。又把那堆画皮卷了夹在腋下,依原路返回,又于路上寻着被那兽物撕掉
的画皮,借着根棍子,连同那泡了屎的白衣一起挑了,到客屋院前,挖了个坑埋
去,收拾停当,又恐另有妖人前来,便又蹲在赵曹氏屋顶,盯盯地守了一夜,待
到东方发白的鸡鸣时分,方才回屋睡去。
却说那「黑里欢」的邪教先是盯上梁府,今番又到赵府兴风作浪,不止谋财,
更要掳人,却不知那艳香雨水邪教如此作怪,其意究竟为何?赵曹氏那满屋子黄
屎恶臭,却要如何处理?那赵仓山不日归来,却又要发生何样事情?欲知后事如
何,请见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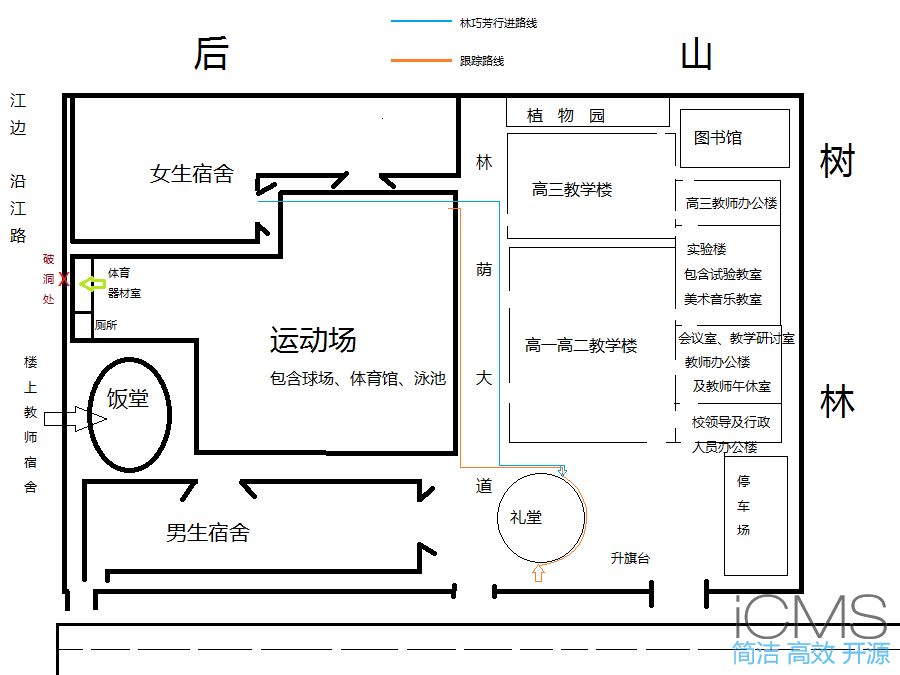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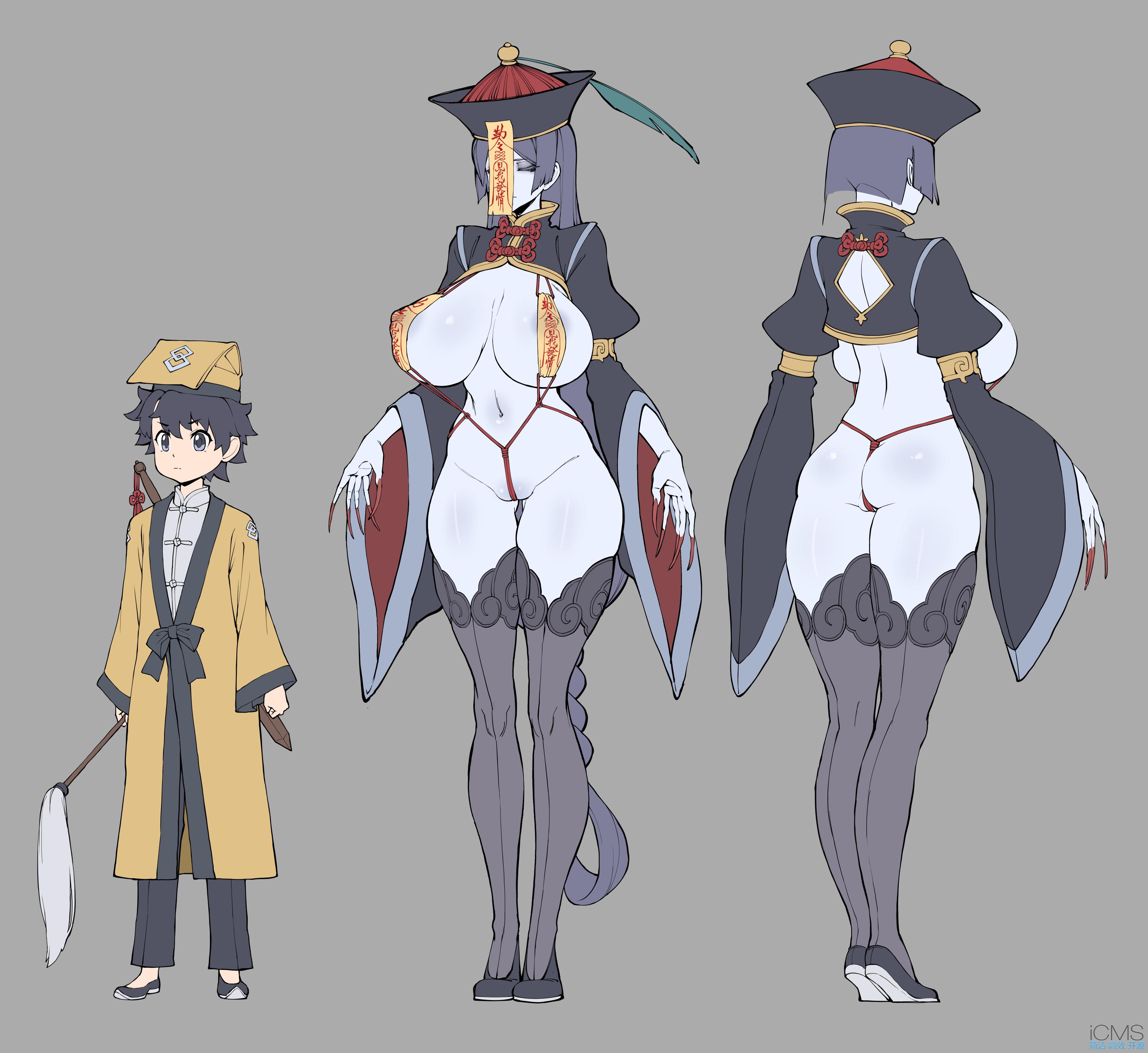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